高晓声:“把人摆到前面的彼岸去”
高晓声:“把人摆到前面的彼岸去”
在新时期文学的农村题材的创作中,高晓声可称得上是根深叶茂、佳果丰硕的作家了。
在二十二年的沉默期中,他真像一块被弃置的盐碱不毛之地,像一片颗粒无收的沙漠荒原……可是当新时期改正冤假错案的“钻杆”在这块土地上轰鸣运转不久,沉睡的大地苏醒了,人们发现这里原来蕴藏着一座富矿,而且马上出现了如原油井喷那般的令人欣喜的景象。《七九小说集》、《高晓声一九八○年小说集》、《高晓声一九八一年小说集》……像精炼过的纯度极高的石油,从作家脑子这座复杂的化工联合企业中源源流出。
高晓声曾以“摆渡人”自勉,他要用自己的文学作品“把人渡到前面的彼岸去”。他认为“一个作家应该有一个终身奋斗的目标,有一个总的主题。”他自己的宏愿是,“就我来说,这个总的主题,就是促使人们的灵魂完美起来。”他在切实贯彻这些创作目标的过程中,既获得了作品的丰收,又通过创作实践对自己的创作目标有了更深的体认,并作了精辟的发挥。这次他不是用的“摆渡人”之类的耐人寻味的形象比喻,而是科学的理论上的阐释:作为一位反映农民生活的作家,首要的职责是“要启发农民进行自我认识,认识自己的优点和缺点,认识自己的历史和现状,认识自己必须努力进步,具备足够的觉悟、足够的文化科学知识、足够的现dai办事能力,使自己不但具有当国家主人翁的思想,而且确确实实有当国家主人翁的本领”。在作家的这席理论阐发中,什么是农民的“前面的彼岸”的具体目标,什么是“灵魂的完美”的具体尺度,都清晰地呈现在我们的视野之中了。除了促使“自我认识”、“自我努力”的首要任务外,作家还提出反映农村题材作品的其他目的:“二是要让我国各阶层的人民,都了解农民的状况。我国是一个有八亿农民的国家,……必须读读农民这本书,才能知道我们能够做什么,步子应该怎么跨,速度怎样才算快,才晓得什么叫正确,什么叫错误。”这种各阶层人民对农民的了解是必不可少的,作家是将它放到“了解我国的国情”的高度去强调的,有志于革命和建设的人们不了解八亿农民状况这一重要国情,岂非盲人瞎马,寸步难行?高晓声说他创作农村题材的目的之三是:“要让大家看到农民思想和习性对于我国整个社会各阶层的巨大影响……不管哪一个人,都在农民的重重包围之中,即使你是超人,也摆脱不了他们的影响……他们身上有许多优良的品性,但也不要否认,历史上种种阶级的陈迹,也受到他们的‘保护’,留在他们中间。”我们之所以用不少的篇幅复述作家的这些见解,一是因为从创作实践出发,比较系统地论述农村题材作品的目的和任务的文章,并不多见;二是因为作家力争要达到的愿望,也是评论者反过来当作衡量作家的作品成功与否的天平,看到的客观效果的重量与主观愿望的砝码,孰轻孰重,抑是两两相平。我们就从这个基点出发,既从农村题材的特殊性,又从文艺内在规律的普遍性,去评价高晓声作品的贡献与不足,他的艺术经验的得失。
一
高晓声让各阶层人民了解农民的状况,是从他们的最平凡的日常生活开始的,从“衣食住行”落墨。但是,陈奂生在饥肠辘辘时,对衣饰打扮并不在意;李顺大为了购买建筑材料,跑断了腿也没有希望农村最好有汽车代步。可见,在当时,农民对“衣”、“行”的改善还没有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亟需解决的是“食”、“住” 问题。高晓声写的陈奂生的“食”和李顺大的“住”,虽非“国计”,却属“民生”。但它们既是八亿农民性命攸关的民生问题,也必然是国家方针大计中的重要课题。因此,高晓声反映的最平凡的农村状况,却引起了如此巨大的震动和深远的反响,就连作家自己也是万分惊诧的。当然,他在写作这些作品时,“自我感觉”是良好的,但对由此而一度掀起的“高晓声热”是出乎意外的。他在谈及写作《“漏斗户” 主》后的“自我感觉”时说:“在写这篇小说之前,我已在‘四人帮’粉碎后写过几篇了。但写出了《“漏斗户”主》之后,我才对自己有了信心,认为这篇小说,只有像我这样在农村几十年,和农民同甘苦的人才写得出,我看到了那种生活在作品里放出光彩了。那真是我自己特有的东西哪!”既是“平凡日常的生活”,又是“自己特有的东西”、这种在“平凡”中挖掘出“特有”的作品,它显现的作家的创作个性必然鲜明;它既然有作家的独特的见地,其认识作用也往往是巨大的。
但是在高晓声的作品中反映“食”、“住”毕竟还不是最终目的。在他看来缺吃无住固然难以生存,但有“食”和“住”也不一定能“促使人们的灵魂完美起来”。高晓声是要想从“食”下手,从“住”切入,进而去表达他的创作的总的主题:希望使农民“不但具有当国家主人翁的思想,而且确确实实有当国家主人翁的本领”。
《李顺大造屋》是以叙述李顺大的命运的焦点--造屋中的苦难历程为其特色的。但作家也深刻地洞察到,李顺大造屋之所以要经历种种磨难,是因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大厦的工程中也出现了失误和故障--“那两次灾难都是由于党的路线出了毛病”。我们希望李顺大的新居早日落成,但也更希望李顺大不做“跟跟派”,更不做逆来顺受的“跟跟派”。所以作家写《李顺大造屋》的重要着眼点之一是,探究像李顺大这么一个“跟跟派”,在现实生活的演进中,他能不能“变”。作家的回答是“审慎的乐观”:在时代潮流的正反两股水流的冲击下,李顺大能唱《希奇歌》,就表明他已从无条件的“跟跟派”变成“被生活逼出了一点觉悟的‘跟跟派’”;他的几句“神来之话”:“现在是地牌吃天牌,烘污二封王……”是李顺大对“文化大革命”形势的通俗概括,说明他已变成一个“开始能够辨别是非的‘跟跟派’”。小说的结尾落在李顺大的扪心自省的责难声中:“唉、呃,我总该变得好些呀!” 李顺大的这种“上进心”,也是作品亮色的重要光源吧?当然我们都不会满足于李顺大们只做“跟跟派”的现状,我们是和作家一样地切望他们能做国家的主人,做开拓新时代的主人!
就《李顺大造屋》和陈奂生系列小说相比,我们觉得李顺大的个性化还未达到陈奂生这一形象的臻美至善的程度。这是因为作家对李顺大的命运倾诉未能与刻画人物性格的笔墨结合起来。我们感到作家将人物的命运像倾泻的瀑布般地冲击着读者心灵的深潭,全文几乎都是用作家热切的介绍表述来代替场景的展现和人物的对白。但是陈奂生系列小说中,却放慢了那太急骤的节奏,注意到让人物在场景中表露自己的性格,显得舒展而酣畅。
在《“漏斗户”主》中,作家对陈奂生作了画龙点睛的介绍:“他和他们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他们的经历(包括他们自己的祖辈)使他们的感情都早同旧社会决裂了。现在,在新社会里,许多人都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而他却愚蠢地没有找到。尽管这样,他还是一点没有办法怀念过去,能够寄托希望的只有现在。所以他一刻也没有失去信心,即使是饿得头昏目眩,他还是同社员们一起下田劳动,既不松劲,也不抱怨。他仍旧是响当当的劳动力……”陈奂生就是这样一类农民的典型代表:既与旧社会决裂,而又在新社会中还没有找到位置的人。这位置不是指某种职业,而是指名实相符的主人翁的岗位。陈奂生系列小说就是写陈奂生的找位置--走弯路--可望找到位置的历程。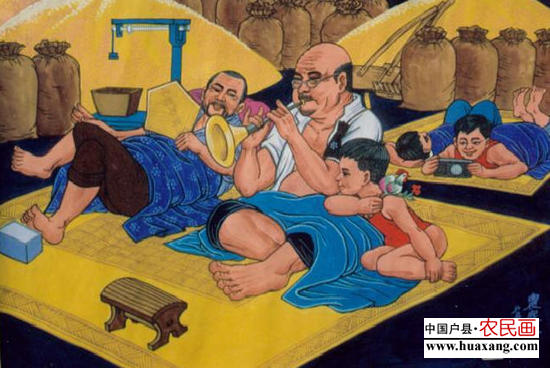
“漏斗户”主陈奂生缺乏主人翁思想是可以想象的。世界上少有饿着肚子的主人。但在粉碎“四人帮”后,他是“三定”落实的受益者,他被摘掉了漏斗户的帽子,但他受益的主要部位是“肚子”,而不是“脑子”。他以解决饥饿为其主要奋斗目标,一旦吃饱穿暖,就无忧无虑,不仅“满意”而且“透了”,再能卖油绳赚几个活钱,他几乎以为自己已经找到了“位置”。可见,小生产者的短视习性和狭隘心理,实在是他无法“以天下为己任”去成为国家主人翁的内在障碍。
作者在刻画李顺大时,主要写他是个政治形势方面的“跟跟派”。但是在陈奂生系列中,高晓声告诉我们:莫看他是出色的强劳力,陈奂生还是个生产上的“跟跟派”,是一架“只管做,光用手,不动脑”的产粮机。“队长指东就东,队长叫西就西,跟着他的屁股转了二十八年了。”大脑只需长在队长头上就够了,他只想做稳队长的伙计就行了。至于政治上,他的“干部比爹娘还大”的名言,更足以说明他的政治上的自卑感。
小生产者的鼠目寸光,政治上和生产上都极度自卑,经济上内亏已极,他还有什么主人翁意识可言。“还是再看看吧”是他的口头禅,说明他是个冷眼的旁观者;他委曲求全,忍辱负重,逆来顺受:“有饭吃,就吃。没有饭吃,就吃粥。没有粥吃,就瓜菜代。没有瓜菜,就吃榆叶、马兰。”即使是当他摘掉了“漏斗户”帽子,高晓声还说:“我写《陈奂生上城》,我的情绪轻快又沉重,高兴又慨叹。我轻快、我高兴的是,我们的境况改善了,我们终于前进了;我沉重、我慨叹的是,无论是陈奂生们或我自己,都还没有从因袭的重负中解脱出来。”
高晓声:“把人摆到前面的彼岸去”
tag: 彼岸 高二同步辅导,高二册同步教学,高中语文知识,语文教学 - 高中语文 - 高中同步辅导 - 高二同步辅导
栏目导航
- ·《锦瑟》新解
- ·一个浪漫诗人的心路历程 ——关于《梦
- ·关于《石钟山记》的另类说法
- ·孔雀东南飞戏剧图
- ·纵情山水间 茶亦能醉人──欧阳修
- ·漫谈《古诗十九首》(迢迢牵牛星|白马篇
- ·游褒禅山记第三段欣赏
- ·张溥之死
- ·巴金、冰心 :一对莫逆之交的朋友
- ·谈白居易的讽喻诗
- ·《祝福》说课稿2
- ·门槛教案
- ·画家雨果——写于雨果诞辰二百年之际
- ·奇傲的梅 |病梅馆记|龚自珍|
- ·歸有光等唐宋派|项脊轩志|归有光|
- ·《孔孟》中引用《论》、《孟》文句的出
- ·名士龚自珍
- ·美腿与丑腿
- ·秦松赋 |登泰山记|
- ·学者字欧阳修
- ·龚自珍纪念馆
- ·孔子生平介绍
- ·藏景阁(14)·以自己的方式独语西北(
- ·李白诗作品选七
- ·梦断槎湾一角青——龚自珍的洞庭情
- ·泰山四大景观
- ·《琵琶行》课件
- ·巴老箴言|巴金